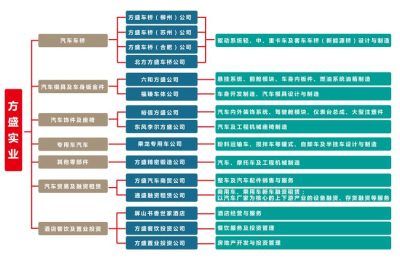《江南儒学的构成与创化》是《江南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何军主编。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介绍了江南儒学的诞生、唐宋时期的变迁和江南儒学的兴起、明清时期江南儒学的演变以及江南儒学的现代探索。本书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导火索,引发学界对江南儒学长期深入的研究兴趣,使江南儒学研究成为江南研究、儒学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乃至未来的一个组成部分。面向中国现代化研究。重要领域。
本推送节选自何军教授撰写的《为什么要研究江南儒学?》一书第一章。
好书·推荐
《江南儒学的构成与创化》
何军主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本书是《江南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第一章主要对江南儒学的介绍、意义和时期进行阐述,希望能够为江南儒学建立一个整体框架,并尝试呈现一些关于江南特色的思考。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叙述江南儒学的诞生、唐宋时期的变迁和江南儒学的兴起、明清时期江南儒学的演变以及江南儒学的现代探索。其中有一章专门论述明末江南儒学和西学。本书希望能够起到一个煽动者的作用,引发学术界对江南儒学长期深入的研究兴趣,使江南儒学研究成为江南研究、儒学研究、中国哲学和思想史研究的基础,甚至是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化研究。一个重要的领域。
为什么要研究江南儒学?
(摘抄)
文丨何君
江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状,构成了提出江南儒学研究最重要的直接外部因素。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中,江南的经济、社会、文化不仅走在中国前列,而且表现出强劲持久的动力;许多源自江南的理念和做法不断上升到国家层面,长三角一体化崛起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彰显了江南立国之本的本质。江南所辐射的吸引力和引导力,证明它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现实为上世纪中叶以来对江南的长期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使江南能够获得更好、更进一步的自我认知。由此产生了江南儒学的概念,以期进一步推进江南研究。
当然,强调江南儒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未来性并不意味着本研究完全以此为基础。相反,江南儒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未来性是建立在历史本身的基础上的,尽管历史上并没有以此命名的学派,甚至没有像江南儒学那样明确的自我意识。仅此而已,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解释。
这个解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历史上南北经济、社会、文化重心的转移及其向江南问题的延伸。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南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不仅长期以来引起历史界人士的关注,而且也引起现代学术研究的关注。相关史料和研究甚多,无需引述。这里我仅根据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的总结做一个简明的总结,以激发我们后续的讨论。《国史大纲》 虽然是上世纪上半叶写的,但钱穆却用他的提纲风格,把这一长期重大历史现象勾勒得很清楚。钱穆指出,中国历史的前半段重心在北方,后半段在南方。这次转变以安史之乱为节点,转变过程非常漫长,似乎直到明朝才完成。 [1] 钱穆把经济指标,如水运、丝织、陶器工业,到文化的各个部分,如科举人数、宰相籍贯人口等,然后对社会上户籍的增减、行政区划的大小、繁简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2]从这一回顾和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南移不仅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而且极其清楚的是,这一南移过程最终以环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
钱穆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转移过程,特别是环太湖流域的江南直到明朝中叶才建立起来,《陈子龙》(1608-1647)等一系列全面论证江南地位的文章出现在明朝后期。陈子龙根据森正男的研究论证,江南地区包括今天的江苏省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省北部,即长江下游南岸的三角洲地区,实际上是太湖流域。陈子龙在多达七篇文章中,不仅系统地展示了江南在综合地理条件、具体水利地质特征、土木建筑技术、蚕桑丝织业、女性才干、水产资源、物品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其在历史进程中确立的重要性,以及明朝政权本身的建立过程及其完整的政治格局,赋予了江南作为大明王朝的根基的地位。换句话说,陈子龙的江南论绝不是从江南角度来讨论江南,而是完全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来强调江南的地位。 [3]
然而,正是因为陈子龙的系列文章才能证明江南真正确立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中心。虽然事实上它已经在形成了,但是它的名声却来得晚了一些,否则陈子龙也不会这么做。一系列的文章,特别是他想用自己的问答方式来为自己辩护。这种晚于实际命名的现象似乎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江南已明确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事实下,为何还要向国家明确其根本地位?可能的解释可能有很多种,但从陈子龙自己提出的问题来看,结合我们的研究对象,似乎可以重点关注两种解释。首先,江南成为经济、社会、文化焦点的中心只是一个偶然、暂时的结果。对于历史上的人们来说,还是有重心回归的期待的。因此,直到明末才认为江南已成为重心。陈子龙还需要证明这一点。二是虽然江南已成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中心,但其经济行为、社会组织和文化形态背后的思想体系并不合法。陈子龙在辩论中强调,江南立国之本“实际上是吴凤娇”“姑树衍”的结果,这种“风教姑树”在陈子龙的论点中固然是积极的,但从北方,可能完全是负面的。 [4]
《松江邦彦画传》 陈子龙肖像
这意味着,江南作为一个地区,能否成为立国之本呢?或者说,江南为何能成为立国之本?或者说,江南是如何成为立国之本的?自然地,它会成为一个问题或一系列问题。从这样一组问题出发,江南研究当然首先是一个区域研究问题。但陈子龙的论点已经超出了地域研究的性质,而涉及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及其内在动力的问题。这是江南学创立的根本理论依据。
另一个方面则集中在“吴凤娇独特”的问题上。前面提到的江南问题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而“文风教化”则指向文化,尤其是狭义上的文化核心,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江南儒学。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认识存在差异,但我们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认识。从陈子龙的论证来看,他虽然从自然环境到制度设计和安排进行了论证,但最终还是将其归咎于“风教”。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提出江南儒学概念的历史依据。如果你仔细读陈子龙的《有吴风教古树》,就能发现他说的是江南的完整,即“吴”,其二则归因于“风”的“古树”。角”。这个“固术”正是江南儒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域所需要面对的。固术的面貌是怎样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坚实性?为什么这种坚实的区分会导致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南移?它在当代还存在吗?它能通向未来吗?
总之,江南儒学确实是一个首先由外部因素塑造的概念,但它也是建立在具有坚实历史基础的学术理论之上的。
江南儒学的提出虽然有现实依据和学术理论依据,但具体研究时其内涵仍需进一步界定。这个定义首先涉及如何理解江南作为一个空间,其次涉及如何理解儒家作为一个对象。这两个问题都很牵涉,所以这里我们只先讨论儒家思想的定义。
儒家思想是一个界限非常模糊的术语。从广义上讲,即就其文化意义而言,它几乎涵盖了传统生活中的一切。尤其是在研究一个地区的儒家传统时,往往很容易指向如此广泛的意义。前述陈子龙提到的“风教”可以对应于此,尽管“风教”的定义可以比文化稍微狭隘一些。但如果从文化意义上来研究江南儒学,那么现有的江南文化研究就足够了,实在没有必要单独突出江南儒学。因此,当我们塑造江南儒学的研究领域时,儒学的内涵不是广义的文化,而是狭义的“学”。借用李学勤的话“儒学的核心是儒家经典”[5],江南儒学的研究对象将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儒家学术思想;取代现代学术分类的,将是从哲学角度研究儒学。然而,明确了这个基本定义之后,紧接着必须要指出的是,江南儒学研究,无论是传统知识意义上的儒家经典,还是学术意义上的现代哲学,都是与当地高度相关的研究。江南儒学不仅与其他知识门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例如传统上对经史的重视几乎是江南儒学不可分割的研究对象,而且在实践中也延伸到了其他知识门类。所要分析的领域,如陈子龙提到的“风角”,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哲学分析的范围。
由此看来,对江南儒学的研究将着眼于对儒家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进行文本分析,以发现和厘清塑造江南本质和特征的内容,但同时也考虑到这些意识形态文本与其真实情况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在处理后一个问题时,或许我们的研究会溢出对思想文本的哲学分析,延伸到对其他文献的处理,以达到思想史研究的效果;我们甚至不排除实地调查,尤其是明清以后,如上文注中所举的例子。毫无疑问,具体的流程要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来确定,明确规定既不恰当也不困难。另外,当我们在江南儒学研究中对儒家观念做出这样的自我限定时,除了儒学本身有这样的基础之外,最根本的考虑之一来自于专业操作。学术专业化可能是避免研究复杂问题的借口,但这确实是一个方便的理由。而且,专业精神最终是现代学术分工的基础。当然,江南儒学的这种自我限制并不意味着其他视角的观察不属于儒学研究。上一篇文章所强调的“文体教学”,实际上也包含了对儒家思想在广义文化意义上的理解。换句话说,多视角观察不仅不被排除,而且是发现和呈现多样性的根本途径。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也会努力。
[1] 对于南北经济中心的转移及其完成的起点和终点,历史学界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对于社会文化中心也是如此。这里的讨论以安史之乱为起点,以明朝为终点,但具体在江南儒学的诞生和演变,将在后面的文章中结合江南的形成来详细讨论。
[2]钱穆用《国史大纲》中的三章,即第38、39、40章,对南迁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论证。其中,对南迁现象和过程的梳理集中在第三十八章《南北》《从唐到明社会的经济文化转移(上)》。
[3]森正夫《陈子龙的江南论》,一石《“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着。
[4] 清末,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江南人口大幅减少。大量河南移民定居在浙江长兴和安徽广德之间。作者的父母是这些移民的后裔。根据作者移居长兴的父亲家族的家谱,作者已是第八代。改革开放前,河南移民基本居住在乡村,语言文化与当地不同。尽管这些移民村基本分布在县城内相对偏远落后的地区,经济水平明显低于当地社区,但在文化上仍然具有属于集体无意识的优越感。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就是他们都将当地人称为“野蛮人”。这不一定构成非常有力的证据,但至少可以提供基于现场的佐证。
[5] 参见《光明网》,2012 年6 月23 日:《李学勤: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
结尾
信息来源:上海书店出版社
编辑:段鹏程